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 |
|---|---|
| 封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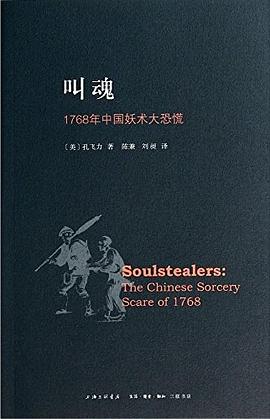
|
| 作者 | 孔飞力 |
| 出版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
| 出品方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
| 原作名 |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
| 译者 | 陈兼 / 刘昶 |
| 出版年 | 2014/06/01 |
| 页数 | 368 |
| 定价 | 38.00 |
| 装帧 | 平装 |
| 丛书 | 孔飞力著作集 |
| ISBN | 9787542643216 |
| 评分 | 9.2 |
内容简介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作者简介
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己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1990)是他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他者世界中的华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书评
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和重复上演。当这位杰出的汉学家试图在两百多年前的史实中寻找解释现代中国历史的要点时,我们身在庐山中,是否能够体会到个中真谛。
1984年,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风尘仆仆地抵达北京,入驻了第一历史研究馆。
面对着充足的清代文献资料,得出“清政府通讯体系”课题——他初始的研究对象——的结论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然而,他尚不满足。对历史的敏感度在提醒他,选择的切入点“剪辫案”中似乎还蕴含着某种隐密的信息,这促使他决定开始梳理整个个案的过程。随即,围绕“叫魂案”的社会群像图就这样在他的笔下徐徐展开。
学者的故事从浙江省德清县的石匠吴东明这里开始,有几起奇案搞得江南一带人心惶惶。石匠被要求将别人的姓名钉在木桩上以达到“叫魂”的效果,石匠将挑事人扭送官府;此事不久后德清人计兆美被诬蔑为“叫魂者”而遭到暴打,从他所听说的传闻中供出吴东明,但编造的供词被戳穿;吴石匠的副手亦遭到同样是非。来自杭州的和尚巨成等人在萧山因和小孩搭话被村民怀疑是“叫魂者”,捕役蔡瑞栽赃巨成使罪名坐实,后被查出是作弊。“叫魂”谣言通过密集的商业网络散布到苏州,张姓乞丐因被小孩指控“叫魂”死于狱中;在湖州,净庄和尚登船时被村民围攻受伤。
从这些现场还原度极高、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故事来看,毫无疑问,学者组织材料的语言能力十分出色。这位名叫孔飞力的汉学大家,自从凭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这块敲门砖带他重回哈佛大学并接替其恩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位置之后,将近二十年未拿出第二部作品,这件事已足够让学界议论纷纷。
好在风言风语并未影响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孔飞力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孔飞力能够像这样只管不紧不慢地执行研究计划,十年磨一剑,是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美国,国际形势和政治关系促成了一种迫切想要真正了解中国这个有着古老历史之大国的需求, 使得“大量的政府和民间基金会资金”资助汉学研究成为现实。 如此以来,为了响应需求,且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吸引社会民众的趣味性相结合,从而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孔飞力便采用了一种不偏离史实的文学叙事方法。这一点与同在中国史研究方面享有盛名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达成共识。“书斋里枯燥乏味的写作使很多话题兴味索然。于是,他(史景迁)便要尝试以新的方式来为公众书写历史。” 史景迁的著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1974年)与《利玛窦的记忆迷宫》(1984)等书均有将社会科学理论诸如心理学与历史史实杂糅的精彩故事框架。与此同时,另一位会讲故事的却不如他们事业幸运的学者黄仁宇, 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1982年)中也从特定年份入手,开始对明史的考量。
不得不说这种“说故事”的尝试是大获成功的。除了显而易见的吸睛作用,这种策略还使得作者站在叙述者的立场上,其责任只是将当时的情况完整呈现,当读者阅读时便是“亲临现场”做一回侦探,可嗅出历史细节中的蛛丝马迹。这样既保持了置身事外的客观,暗中又已经将自己的提炼组合材料的史学家身份映射其中。
用这些奇事作为引子,孔氏已成功地营造起恐慌氛围。他继而简要提及“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这一节几乎是强行插入,虽是由前面的故事推导得知,但后文已有类似论述,私以为应和后文放置在一起方才更有利于理解。实际上,书中许多地方均有此类不太恰当的安置顺序。按照第九章起始所述,全书包含三个版本的故事,即恐惧的普通百姓、相信谋反的皇帝和上下为难的官僚,想要将这交叉进行的三者完全分开来叙述是不太可能的,但至少应有更清晰的分类叙述,方能厘清三个阶层的差异。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许这正是孔飞力的叙史策略之一,即:“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是由⋯⋯人们之间的关系所建构而成的。” 为了表现这种错综复杂互相影响的“关系”,也只得选择这样交织不明的叙述方式了。这样做的损失也只是花去有心的读者一点整理思路的时间而已。
接着,在读者迫切期待“叫魂”事件的后续推进时,孔飞力毅然按下了暂停键。他开始思考“叫魂”恐慌爆发的社会原因。第二章“盛世”便旨在说明干隆年间的经济状况,人口增长、通货膨胀、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冲击着盛世的幻象,这使得民众感到焦虑,引起社会骚乱。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孔飞力竟然否定了社会原因在“叫魂”恐慌中起决定作用的结论,“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却是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 这一最惯用又简单省事的分析手段,在孔飞力的叙史中,仅仅充当了充分非必要条件。他真正要探讨的,是伴随盛世而生的“观念”。
与“观念”并驾齐驱的另外两个隐藏词汇是“事件”和“关系”。 “观念”在“事件”中得以反应,并对其进行加工使之转化成权力和地位,而“事件”又是建立“关系”的契机。这三个名词萦绕在孔飞力的脑中,迅速助他支撑起了后文的解说。
从弘历来看(第三章),“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 “汉化”、 “谋反”两个“观念”是促进弘历下令对叫魂进行清剿的“事件”,也是通过清剿“事件”来巩固皇权专制,防止常规化,从而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关系”,并且借叫魂“事件”发泄自己因官僚制度产生的挫折感和对军事失利的不满(“观念”); 从官僚来看,对上隐瞒息事宁人和对下安抚保持稳定的“观念”促使官僚编造“事件”,屈打成招酿成冤案以应对皇帝的责骂,同时又要为百姓界定“事件”严重性并宣称不能轻饶罪犯以给他们一个交代,从而维护自身处于上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官员与官员之间保持步调一致,形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以对抗皇权的控制;从普通民众来看,大范围弥漫开来的恐慌“事件”反应了对超自然力量恐惧的“观念”,从没有权力的百姓似是抓住了一个使用权力的机会,平日对某人的敌对情绪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故叫魂成为民众“关系”的转换点。而所有的转化最终集中到了权力和地位上,因而我们看到,在以权力和地位为中心、三个名词为线索的叙述中,孔飞力把中国官场——他所谓的“官僚君主制”——说了个透彻。
在这个过程中,孔飞力用词是十分小心翼翼和耐人寻味的:
但他(傅恒)与弘历的密切个人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更为有力的感情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弘历对死去才一年的傅恒的妹妹、他的第一位皇后的记忆。⋯⋯跪在傅恒面前的三个人正好处在中国社会阶梯的另一端。
从这个例子看出,当他在描述一位出场的官员时,特别强调官员和弘历的密切“关系”,而重人情不重法度恰好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可见孔飞力在洞察官僚君主制的运作后,是极其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叙述做到贴合实际的;而接下来一句中对三个人社会地位的强调则是在暗示,当不同阶层面对面沟通时依然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同时这也和前文形成对照,矛盾此消彼长。
书中后八章所包含的内容自然远远不止我这样简单的概括,在此我只是将关注点放在孔氏的叙史策略上。行文看似凌乱纠缠,实则有密线串联,阅读中实在需要读者细加揣摩。那么,姑且认为我的推想正确,我虽不能得知孔氏是如何确定以上几个关键词作为,但我依然被这样别出心裁和新奇独特的思维震惊了。正如葛兆光所说,“在宗教心理学中这样的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在异常文化现象不再仅仅被冠以『落后』或『怪异』而取消其发生合理性的时代,则要求研究者寻找另一些解释思路。” “叫魂”作为一个民俗事件,自然可以从宗教方面予以深究,但出于某种全新的视角,孔飞力在此根本无意探究“叫魂”案件本身,所以他才一再跳转话题,在叫魂事件发展过程中“随意”按下暂停播放键,但他的娴熟程度无疑是做到了用新思路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迂回曲折。
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帝和官僚在“常规化”和“反常规化”的斗争中搅得如火如荼不可开交时,孔飞力又提到这里面存在一种特殊的官僚,他们位高权重,且在自己的领域十分权威,在“叫魂”案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危急时刻,以一种“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自信,“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 皇帝无可奈何,只得悬涯勒马。大学士刘统勋和江西巡抚吴绍诗就是极好的例子。刘统勋识破了各地官僚的上奏中不属实的地方,并且赶往承德陪伴弘历左右防止皇帝“陷入更大的窘境”; 而吴绍诗则是坚持宣称本省并无叫魂案发生,面对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权威,皇帝只是轻微职责几句,并未像对待其他官吏那样言语奚落。
孔氏不动声色地提到这两个人,意图指出中国官僚君主制的最后应急机制实际上依靠的仅仅是菁英文化。而一旦这种菁英文化不复存在,中国政治制度长久以来赖以修护不足的关键环节就随之崩溃,这让人联想到民国时期,身处学术前沿的知识分子打倒文言文的目的就是冲破传统中国的菁英阶层对文化霸权的垄断,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和无所适从的时代。至此,我们似乎在孔氏的叙史中找到了越来越多与现代中国的相同之处,人们对1768年“叫魂”事件前因后果的感同身受也在宣告着孔氏叙史策略的大功告成。
1996年,三联书店敲定的译者来到孔飞力办公室,叩响了门。孔飞力一边将整整一箱按书籍中引用顺序码放的清代宫中档案复印资料交给译者,一边问道:“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译者不禁一震,难道真有含沙射影这等事?后仔细研读,竟果真发现诸多与现代中国社会之相似之处。孔氏成书之际,中国刚刚经历文革那个由不寻常的狂热导致的混乱且黑白颠倒的历史时期,深受其害的中国人又岂非其中的推动者?孔飞力以置身事外的叙述者身份,书成身退,留下无限回音。
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和重复上演。当这位杰出的汉学家试图在两百多年前的史实中寻找解释现代中国历史的要点时,我们身在庐山中,是否能够体会到个中真谛。